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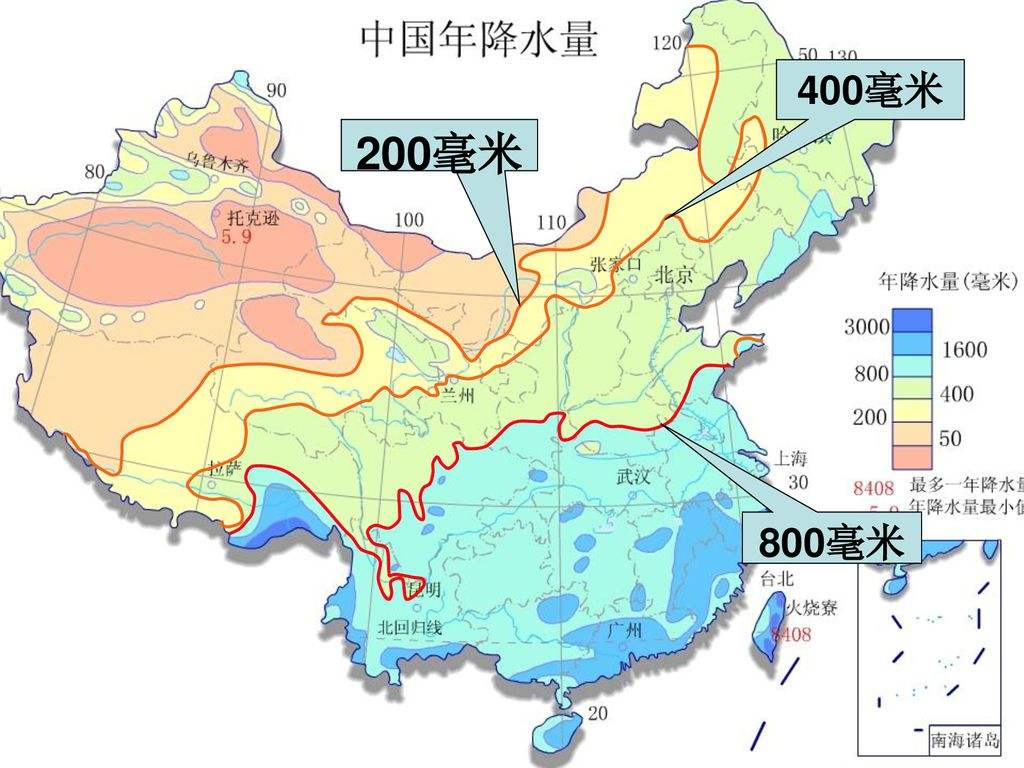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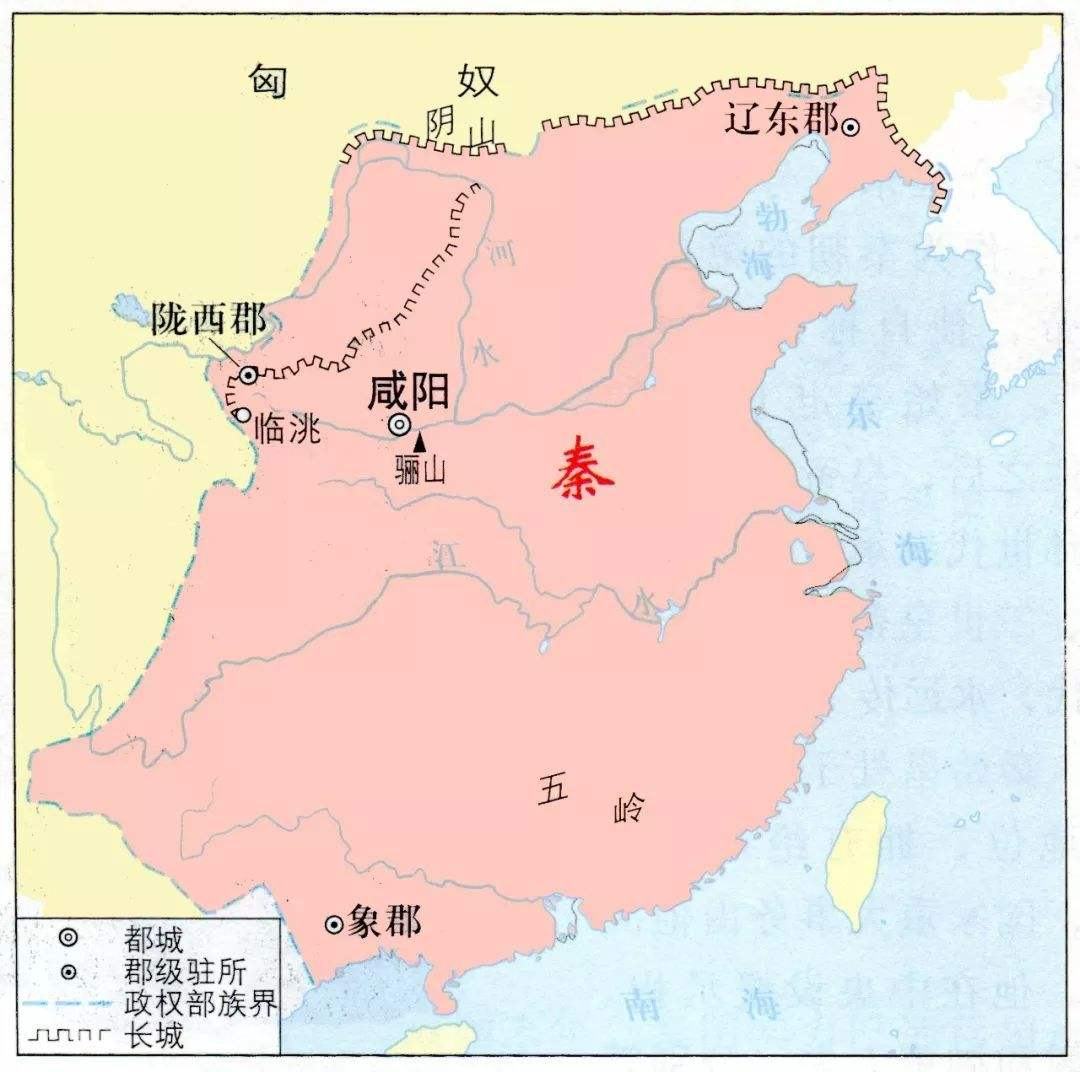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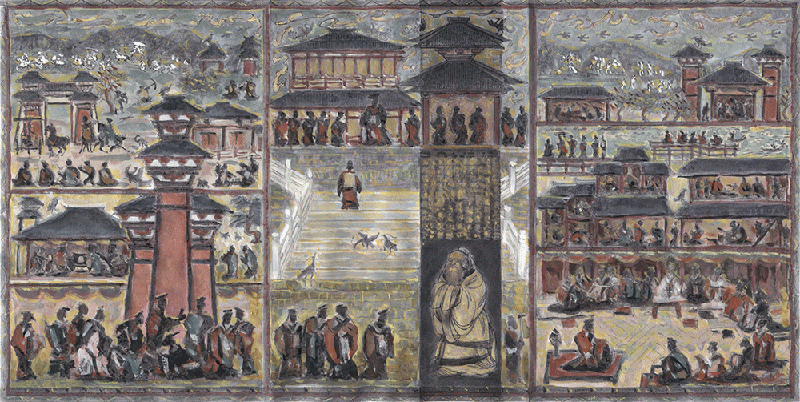
 古时汉族男子20岁称弱冠,表示成年,也就是说这会霍去病还是个未成年人
古时汉族男子20岁称弱冠,表示成年,也就是说这会霍去病还是个未成年人

 也是靠南宋开国君主完颜构的努力才能完成大宋的又一轮内卷
也是靠南宋开国君主完颜构的努力才能完成大宋的又一轮内卷
 大宋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 ,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垂拱殿……
大宋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 ,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垂拱殿…… 甚至小有富余
甚至小有富余
 马嘎尔尼访华
马嘎尔尼访华  虽说那会我们以为世界也就这么大
虽说那会我们以为世界也就这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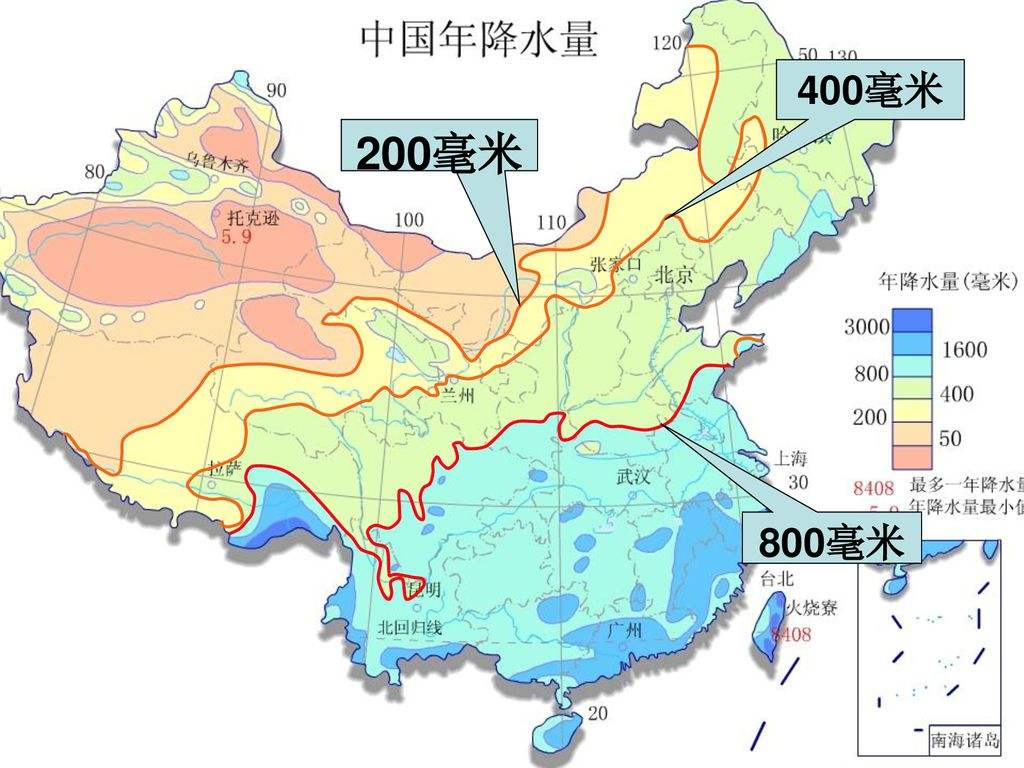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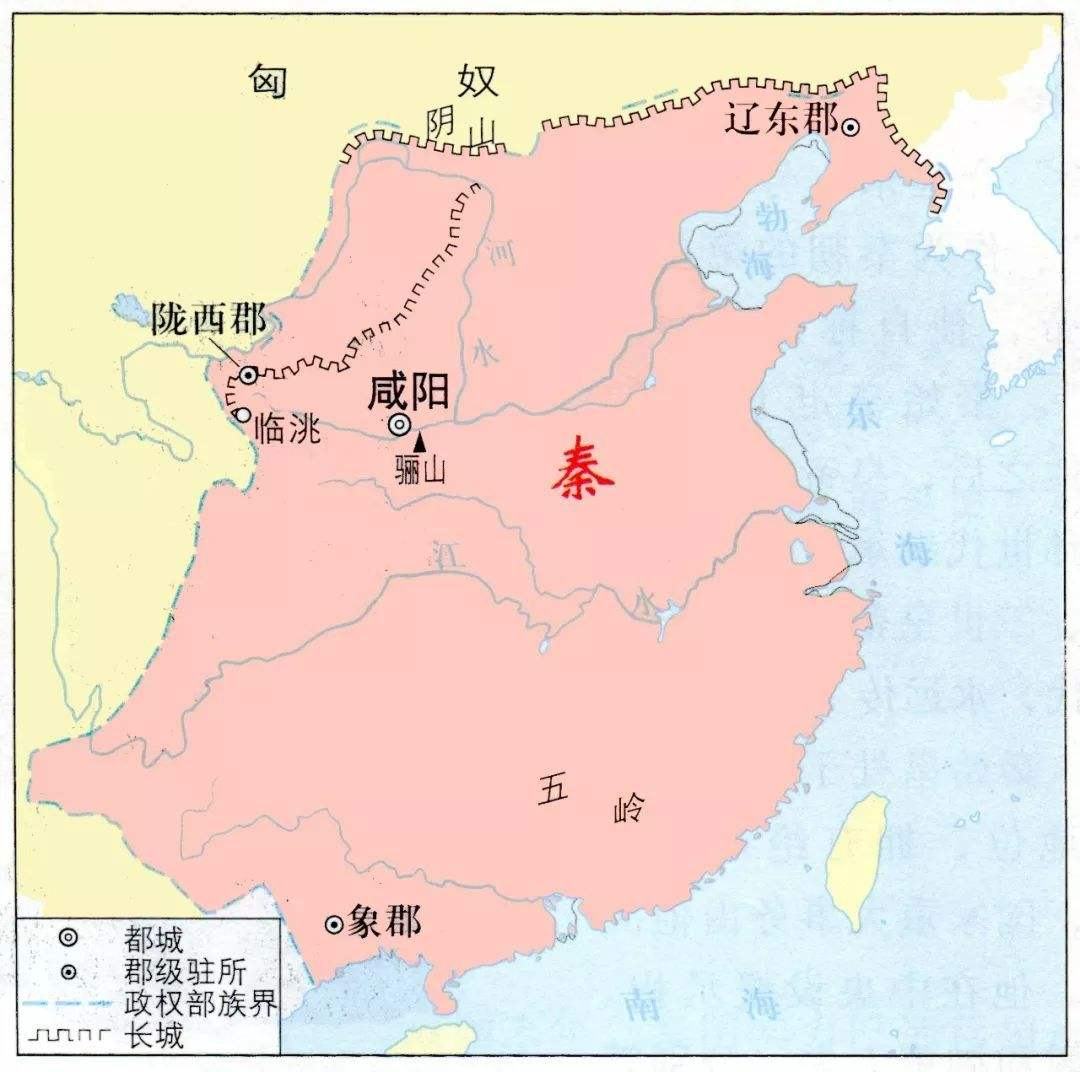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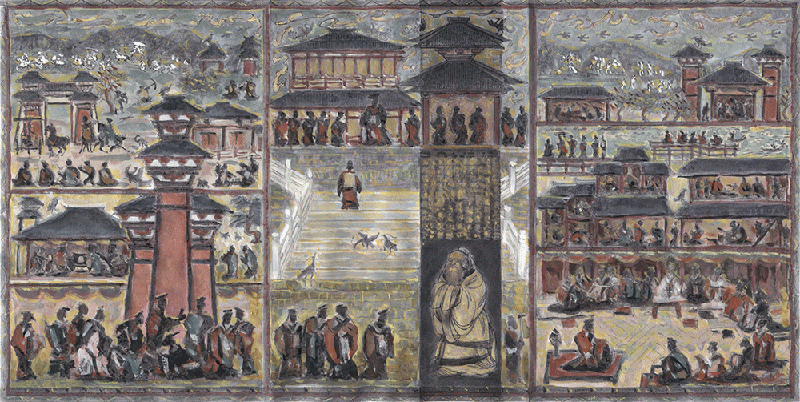
 古时汉族男子20岁称弱冠,表示成年,也就是说这会霍去病还是个未成年人
古时汉族男子20岁称弱冠,表示成年,也就是说这会霍去病还是个未成年人

 也是靠南宋开国君主完颜构的努力才能完成大宋的又一轮内卷
也是靠南宋开国君主完颜构的努力才能完成大宋的又一轮内卷
 大宋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 ,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垂拱殿……
大宋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 ,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垂拱殿…… 甚至小有富余
甚至小有富余
 马嘎尔尼访华
马嘎尔尼访华  虽说那会我们以为世界也就这么大
虽说那会我们以为世界也就这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