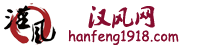中美之间,近些年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
2016年南海军事对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那次事件以中国胜利告终,确立了中国在近海军事力量上超越美国的这个事实。也正是那次事件以后,美国在第一岛链以内就不敢再与中国真正交锋了。
占豪曾在2021年将那一年定义为中美攻守易势之年。那一年,以3月18日杨洁篪主任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回怼美国说“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谈话”为标志,中美大国从战略上攻守易势。中美攻守易势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是自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打出来的!
在2024年的年终10万字文章《大国终极对决》中,占豪又把2025年定义为“大国终极对决之年”。这个重新定位的标志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期全球战略的大幅度调整。
那么,什么是“大国终极对决之年”呢?“大国终极对决之年”不是这一年完成对决,而是从这一年开始,大国之间的博弈和过去的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国终极对决开始后,也就是2025年以后的大国博弈,以及大国博弈影响下的全球格局,往往不会有像过去那样的来回拉锯、拉扯,而是双方一对线就出博弈结果。换句话说,这就像下围棋一样,现在是到了中盘以后了,大国对弈往往很快就会出结果,会立刻形成“提子”。就像乌克兰,特朗普一上台,他就成了美俄交易的筹码,成了最大的牺牲品。这就是“大国终极对决之年”开始后的世界博弈形态,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
在这种大国博弈背景下,依然有人提出一些疑问,譬如就有人觉得,为什么面对美国的加征关税,墨西哥都主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而我们却没有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去和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沟通呢?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墨西哥去找美国谈判有墨西哥的原因,而我们没有去则是我们的现实情况决定的,下面占豪就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与战友们商榷。
一、墨西哥视角:结构性依赖下的被动谈判
首先,从墨西哥的视角看,其在贸易结构上严重依赖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形势被动,他也不得不去谈判。墨西哥对美贸易高度依赖到什么程度呢?2023年,墨西哥对美出口额占其总出口的80%以上,其中汽车、电子产品和农产品等核心产业深度嵌入北美供应链。例如,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75%直接供应美国车企,一旦美国加征关税或设置贸易壁垒,其产业链将面临系统性风险。
此外,墨西哥对美贸易顺差约占其GDP的3.5%,若失去美国市场,国内就业和财政平衡将遭受重创。这种结构性依赖,迫使墨西哥在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只能被动接受美国主导的《美墨加协定》条款,包括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和原产地规则。所以,无论美国开出什么条件,墨西哥都得谈,甚至都得遵从。这种情况,在特朗普上个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特朗普2017年第一个任期一上台就撕毁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然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只能按照美国重新拟定的协定再签一次。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与墨西哥完全不同,近些年我们通过多元化市场布局(如东盟、欧盟、“一带一路”国家),大大降低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2023年,对美出口占我国总出口比重已从2018年的13.7%降至11%,而在2008年中美贸易份额占我国总贸易份额的比例则是超过20%,经过近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能力避免类似墨西哥的“谈判强制力陷阱”。客观而言,当前的中国在面对美国时,我们是有能力和心理优势的一方。
二、风险分散视角:去单一化战略与外贸韧性提升
过去些年,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主动降低了对美贸易依赖的成效非常显著。2023年,中美贸易额为60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2.2%,而同期中国对东盟贸易额保持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更是高达19.47万亿元,增长2.8%,占进出口总值的46.6%。对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3.44万亿元和1.98万亿元,分别增长6.8%和7.1%。由此可见,我们贸易去单一化战略是成效显著的,我们的外贸韧性也是明显提升的。
更关键的是,中国通过“产能转移+转口贸易”重构全球供应链:例如,越南对美出口的电子产品中,约30%的零部件来自中国,东南亚转口贸易使中国对美直接出口占比隐性下降。这种“间接出口”模式既规避了美国关税冲击,又维持了产业链主导权。近几年,我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整体维持在700亿美元左右,这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对越南贸易顺差。
此外,中国外贸结构也正在加速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2023年,我国“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的出口增长29.9%,对冲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滑的影响。数据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从2018年的2.38%降至2023年的1.83%,系统性风险显著降低。
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出口1.48万亿元,增长15.2%。跨境电商进出口对我国外贸增长的贡献达到11.9%,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我国保税维修、保税再制造、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也都在蓬勃发展。
三、博弈能力视角:不对称依赖下的战略主动
过去几年,中美博弈的激烈程度虽是不断增加的状态,但中国在关键领域的自主突破,大大增强了我国对美博弈底气。以半导体为例,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成熟制程芯片产能提升了40%,华为通过自研芯片实现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回升至国内第一,直接削弱了美国技术封锁的威慑力。
事实上,2018年中国制造芯片才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3%,出口规模5500亿元,主要集中在低端芯片领域。到了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1594.99亿美元(11351.6亿人民币),翻了一倍,一举超过手机的1343.63亿美元成为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同比增长17.4%,创下历史新高,保持连续14个月同比增长。同时,2024年中国芯片产量接近4300亿颗,也成为世界第一芯片制造国和出口国。我们的制造工艺越来越好,中高端的光刻机技术已正在获得突破,中高端芯片产能快速增长也就是未来两三年的事了。
同时,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效应”形成反制筹码: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占其总出口的五分之一,仅大豆一项就支撑了30万美国农民的生计。这种“你中有我”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中国在谈判中可采取“非对称反制”——例如还可通过限制稀土出口、暂停采购波音飞机等手段,精准打击美国核心利益。商务部明确表态“任何磋商须基于平等互利”,拒绝接受单边施压,正是这种战略自信的体现。
四、产能布局视角:全球化网络对冲地缘风险
中国通过“双循环+区域化”重构产能布局。一方面,国内推进“东数西算”“新基建”等项目,强化内需市场对高端产能的消化能力;另一方面,对外投资向东南亚、中东欧倾斜,2023年中国企业在越南的直接投资金额达到50亿美元,同比增长30%;根据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的数据,2024年中国对匈直接投资52.8亿欧元,占匈吸引外国投资总额的51%,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匈的最大外资来源国,一大批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企业在匈落地。
这种布局使中国既能规避美国“友岸外包”的围堵,又能通过区域产业链协同维持出口竞争力。例如,中国光伏企业通过马来西亚、泰国基地向欧美出口,既符合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本土化”要求,又保持成本优势。产能的弹性调配使中国无需急于通过谈判解决局部摩擦,反而能以时间换空间,等待美国内部利益集团(如农业州、科技企业)因长期损失倒逼政策调整。
事实证明,面对美国的时候,我们越能保持战略定力,越能让美国无可奈何下主动与中国沟通谈判,反而有利于降低他们对中国的诉求。就像最近,当美国一次一次以所谓芬太尼为借口向中国施压后,中国顶住压力,用一系列事实证据证明我国芬太尼管控极其严格,美国以此为借口打压中国根本没有现实基础,美国没有理由将自己的问题甩给中国。结果,就在最近,美国又主动派了使团到中国沟通,在这样的博弈中,中国逐渐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中国不主动发起对美贸易谈判,本质上也是这个道理,这一切都是我们综合实力跃升后、在做了一系列的布局安排后的策略选择:通过市场多元化对冲依赖风险,以技术自主性构筑博弈筹码,借全球化产能布局分散压力······这种“非对称博弈”模式,既避免了墨西哥式被动,又为争取更高层级规则制定权积蓄能量。未来,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领域加速突破,谈判主动权将进一步向中方倾斜,美国面对需要与中国谈判沟通时会变得更加积极。中国现在做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稳坐钓鱼台,从而形成对美国越来越多的心理与现实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