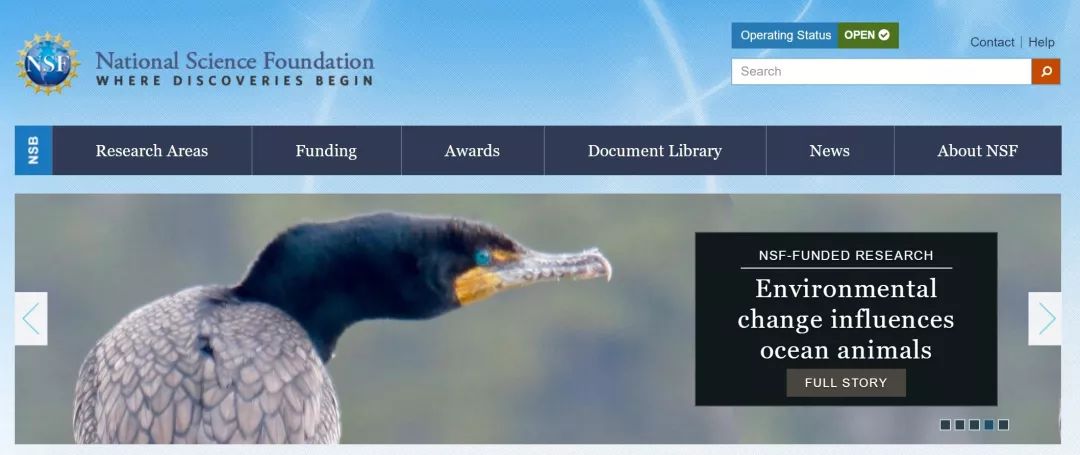告别了七年的科学传播与科技政策的博士训练,我即将离开康奈尔大学,回国继续投身科学传播事业。这七年来,我一直根据自己的实践经历与学术训练,思考中国与西方科学传播体系各自的优劣短长。
正巧,在这一阶段,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一篇网文“中国做对了什么”在知识圈中热传,探讨了近40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我也借用这个时髦的问题,来探讨下中国科学传播做对了哪些方面,又在哪些地方不尽人意。
要说中国和西方在科学传播上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在政治上提升了科学传播的意义。美国有感于科技在二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战后不久就开始推动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当时受到各种专业学会的崛起冲击的美国科学促进会面临转型,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
中国也当仁不让。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准宪法《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规定了国家的任务包括“普及科学知识”。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时科普也成了科协的核心使命。
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1949年9月30日《吉林工农报》
今日西方政界,除了个别具有极端信仰抵制科学界部分主流结论的政客外,科学传播的政治正确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中国则更上一层楼,在世界上率先推出《科普法》,近年来,最高领导人更是屡次在讲话中直接把科学传播提升到与科技创新本身一样重要的地位。
科学传播的这种核心价值的重要性,不仅让科学传播获得更多资源和组织动员能力,还让科学在各个层次的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了正当性。举例来讲,我们经常会哀叹当今中国社会过度娱乐化、影视和媒体不去彰显科学的价值。殊不知,我们有底气来谴责其他文化产品僭越科学的现象,恰恰是因为科学的这种核心价值取向对我们年复一年甚至代复一代的浸润。
笔者与同事经由果壳网及其他途径发放问卷获得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科学传播的崇高的核心价值,让高达97%的中国科学家认为从事科普具有道德正当性和重要的社会意义。虽然在实践上,由于缺乏诸如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那样强制性地对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公众教育(public outreach)的要求,实际从事科学传播的中国科学家数量并不多,但这种正当性完全可以在条件适宜时激活科学家参与到科学传播之中。实际上,NSF的强制性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科学传播在美国科学界取得了重要的道义正当性的结果。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SF官网
所以,经过多年实践又回炉做学术反思后,笔者现在愿意坚定地认为,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上对科普或科学传播核心价值的弘扬,无论如何称得上中国做对的一件事。
当然,做对了不见得就做得好。因为要落实这种科学传播的核心价值就需要一套有力的行政体系。而在实践上,行政体系有可能更关注自身的发展而相对忽视其所推动的科学传播事业的内在规律。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该从中国体制与社会的特殊之处对此加以理解。
虽然在中国,科学传播的行政体系有时会受到专业人士的批评,但不得不承认,这套行政体系的组织动员和社会渗透能力,远远超越了西方同行。按照2018年出版的《中国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给出的数据,2015年,中国已经拥有了科普人才205万人,其中专职人员22万人,兼职人员183万人。按照中国2018年拥有418万全职科研人员数量来算(数据来自科技部,近年来这一数量变化不大),科普工作者数量相当于将近一半科研人员数量了。
实际上能成为兼职科普人员的全职科研工作者应该远远达不到一半人。那剩下的差额哪去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基层科技工作者,包括农技站、卫生防疫系统以及一些基层厂矿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科学传播(科普)从制度安排上讲是下沉和渗透到最基层的社区的。
当然,国内学者曾有调研指出,中国很多基层科普做得很勉强,一些农业科技讲座还需要给听众付钱。但能付钱鼓励最基层听众这一点,本身已经说明了基层具有了相当的组织动员能力。
然而,在科普能深入基层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却与科学家疏于参加科普矛盾。
对科学家疏于参与科普,常见的解释是缺乏制度性激励,以及科学家工作太忙。但同时,我们的调查显示,也有其他因素值得思考。一是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缺乏科普渠道,另一点是他们认为媒体不可靠。
这两点因素,实际上指向了现有的科学传播组织动员网络的不足——尽管这个网络体系有强大的基层渗透和动员能力,但它要依靠科学传播的行政体系,而这样的行政体系实际上与科学家日常活动是分离的,很难调动科学家。
不仅如此,依靠行政系统运转的科学传播组织动员体系,在科学界的落足点放在了各级学会,而中国科学界由于体制的原因,学会发展先天不足,后天也没有像美国科促会那样,将科学传播作为自己活动的主要支点。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有的中国科学传播系统在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科学界自发科学传播活动的替代或挤出效果,而科学界自发的和基于科研机构自身(而不是专职科学传播机构)的科学传播活动,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科学传播活动非常活跃的主要原因。
科学家对“媒体不可靠”的判断也与中国科学传播体系的组织有关。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属于科协系统的各级科技报系统,隶属于科学院的中国科学报系统,以及属于科技部体系的诸多报刊,这些是科学传播的“自己人”,一般不会被科学家们认为不可靠。但大量的市场化媒体则因为其科学素养低下又追逐新闻热点而不受科学家们待见。这些数量更大、更活跃的媒体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到科学传播的体系。这也是依靠一套行政系统发挥组织动员的中国科学传播体系涵盖不足的地方。
除了媒体动员不足外,这套动员系统对官方体系之外的力量调动也是不足的。以全国科普经费为例,2015年全社会科普经费141.2亿,其中75.5%来自政府。全社会科普经费捐赠仅为1.1亿元。
对此,笔者有着深切的体会。如果向中国的民间基金会(如阿里或腾讯等)申请基金,科普项目一定要被包装成环境教育或者社会公益项目(狭义的,敬老扶贫型),因为科普浓烈的官方色彩,使得这些基金会认为,科学传播本身不关我事。
本文还要指出的被长期忽视的一点是,中国科学传播的整个体系缺乏对个体受众的传播效果的评估。翻阅多年的“科普报告或蓝皮书”,我们会发现,它们对活动经费、活动内容和参加人数如数家珍,但对活动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什么影响则鲜有提及。
这可以说是中国大多数官方活动的特点——重组织,轻个体效果。我们从来没有常规的舆论调查。就科普事业而言,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受短缺思维主导,觉得如果能给人们提供了这些过去没有的科普手段,就是巨大的进步了。但殊不知,在互联网和无线网络让获取信息的代价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信息的说服效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拿转基因领域来说,相比其他科技活动,它显然得到了更多的科学传播经费和资源的支持,但中国又有多少公众认可了转基因的安全性呢?
忽视对科普活动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还会带给我们另一个难题或者盲区。历年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总体上呈现了不断进步的趋势。在对这一成就感到欣慰的同时,笔者对于到底有多少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来自全国各种科普活动,心里完全没有底。也许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尤其是获取信息途径的多样化和成本的不断降低,自然会带动科学素养的提升。假如果真如此,有组织的科普活动需要获得纳税人支持的合法性在哪里?无疑,专业科学传播机构有义务来论证自己工作与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的相关性。
在读博前多年的科普生涯中,笔者曾一度认为,中国科学传播工作的核心缺陷,就是缺乏公众参与。
但这一理想被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经历打脸。在实践上,笔者参与组织或报道过的有关转基因的各种对话和辩论,不是演变成闹剧就是以激烈对立而收场。在国外,以发起和组织公民共识会议而蜚声国际科学传播界的丹麦技术委员会,在2012年因公众对其各种科学对话的实际参与度很低,被政府取消了资助。
这实际上是“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模式带来的困惑——科学传播工作者可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公众参与很重要,但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那些与自己生活无直接关系的共识会议或科学对话并没有吸引力,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即便有人愿意参加,但谁是公众代表?何为科学问题上的民意?对话产生的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些都是迄今为止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未解的难题。
既然如此,在本来就不鼓励公众参与的中国社会,是否还有必要发展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动,或将其作为科学传播的目标?
首先,在很多涉及科学的领域,公众参与已成必然。比如各地有关争议性技术的民众抗议,有些还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街头政治的形式。虽然科学传播工作者还没有把公众参与明确写到方案中,但环保法规中——如生态环境部2018年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公众深度参与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科普工作者回避公众参与已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失职。
其次,公众参与不应该作为目的,而是仅作为一个手段。任何科学争议,都绝非有了公众参与就获得了解决方案。公众参与毫无疑问能促进交流对话,但同时也会带来极端情绪的扩散。因此,何事上需要参与、谁来参与、如何参与、如何评估参与效果,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个案讨论。
第三,在正视公众参与科学面临的困难时,也应该看到,有效和有组织的公众参与,有助于促进公众对科技与环境政策的接受,而反过来则可以把公众本来接受的事情搞砸。最近的上海市垃圾分类的执行就体现了这方面的困境。在垃圾分类条例执行前,笔者恰好看到一项用微博大数据分析中国环境舆论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官民在垃圾焚烧一事上长期对立后,在垃圾分类的正当性和可行性上达成了高度一致。然而匆匆实施的上海市强制垃圾分类措施,却因为事先没有足够的民意铺垫而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这一共识。
与中国科学传播体系在调动科学家和非商业的社会力量(非官方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方面的不足看似矛盾的是,市场化力量在过去几十年的科学传播工作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推崇市场力量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在这一前提下,科学在意识形态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引诱着诸多弄潮儿,让他们相信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地位也能在市场上变现。笔者曾经也是其中一员。
在中国,由于体制原因导致公民社会发展不平衡且集中在公益与环保领域。市场化的科普力量在填补官方与普通公众需求的隔阂时发挥了重要力量。当然其中也诞生了很多伪科学、伪养生的糟粕。但无论如何,中国科学传播体制对市场化的接纳是正确的一步。
科学传播官方机构在市场化方面还有些扭捏,相比之下科普界官民商学各类人等在拥抱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算法新闻等新传播技术方面却相当积极。从本世纪第一个10年推动互联网科普下沉基层社区,到如今上百个科普类公众号的遍地开花,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移动互联网和公众号的兴起导致了传统媒体全线式微,科学新闻媒体或科普网站自然不能幸免。但这对于科学传播这也不失为一次机会。
首先,新媒体的精准阅读功能让科普和科学新闻更容易找到特定的读者。
其次,更加重要的是,新的公众号等低成本媒体极大地解放了原来被压抑的科学新闻采编人员,也将不少愿意从事科普的科学家调动起来,甚至将其打造成科普达人。在大多数传统媒体,从事科学新闻采编的人往往都是比较边缘化的,经常要被临时调用从事其他报道和编辑。但如今,很多仍然留在媒体的科学传播人都办起了自己的公众号,而专业的公众号在得到了投资支持后,还可以通过基于科学界的资源影响层次较高的大众。这与原来的党报党刊或科技日报等专业媒体完全不同,是市场借助新技术手段自发的对资源进行配置。
公众号和传播模式的变化,还带来了科学传播风格的嬗变。如今在科普类公众号上,哪怕贴出一条中国科协的项目申请通知,标题中不来几个感叹号或省略号仿佛都不好意思。标题党的做法为很多传统媒体人深恶痛绝,笔者在科学传播领域却愿意乐见其成。这不仅有助于改变科学冷冰冰的面孔,激发人们的兴趣,实际上也意味着官方体系对科学传播话语垄断权的减弱与消融。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配备了各种“网络利器”的中国科学传播体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迄今为止,从互联网到算法传播的信息通讯技术,让中国的科学传播体系第一次实现了对科学家自发从事科普和受众主动寻求科学信息的双向动员。即便有助长网络谣言和冲击传统媒体这两大“罪状”,对信息通讯技术的拥抱也是中国科学传播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除了弘扬科学传播的价值、建立起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以及拥抱市场化和新技术外,中国科学传播当然还做对了很多事,比如对国际经验的虚心学习和对科学主流观点的坚持。
同样,中国科学传播没有做好的地方,也不止是本文所讨论的对科学家参与科普的动员力以及公众参与方面的不足。指出这些没有做好的地方,并非否定中国科学传播机构和广大科普工作者的成果,而是着眼于进一步提升已有的成绩。
比如,中国的科学传播体制已经具有了举世无双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我们仍然要研究和尝试,如何更好调动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其实首先要明白,他们参与科普的动机和动力到底是什么?无疑,要让中国的科学传播取得持续的进步,明白我们作对和做错了什么,以及了解我们在认识上还存在哪些盲点,这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