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纪念日了,我作为一名党员,今天当然要来谈一谈我们的党。
我们今天正好又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百年了,人类积攒的所有的知识、挑战、经验,仿佛都是为我们准备的。别人看着我们,满怀羡慕嫉妒恨。
之前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门非常有趣的知识领域;而在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实践的党的历史,是一个更加有趣的知识领域。

它包括各种历史记录、各种文献、会议资料,尤其是很多党内人士的口述史,这里面有的人和党一路走到底,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
比如有一位叫做郑超麟的老党员,他就离开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郑超麟回忆录》,里面记述了很多早期党员的这些八卦轶事,很有趣。
很多早期党员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没有经历过那种血与火的实践的磨练,他有激情的一面,也有很天真的一面。

比如郑超麟就写道:有一些早期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搞自由恋爱,他们是真的按照恩格斯在讨论家庭和婚姻的那篇文章里写的说法:要去打破婚姻枷锁。
所以特别的自由,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还经常换来换去。但是这个风潮很快就过去了。
共产党也分为前后好几波,后来的党深入农村和人民走在一起,就大大地变化了。
有人批评共产党封建化、保守化,他们可能不知道比如延安时期的《婚姻法》,一开始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婚姻法》。
我之前还给大家讲过《何长工回忆录》,那故事多有趣。
何长工还参与了共产党攻占长沙的行动,这是共产党军队在进攻方面的早期的高光时刻,由毛泽东布置,彭德怀指挥,趁着国民党军阀在中原混战,他们一举攻占长沙。
当时何长工召集外国的领事、记者、医生、教会人士几百人,他用英文、法文两种语言对大家演讲,告诉他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求他们配合。
结果当时很多外媒都报道了这个事情,西班牙的报道就说共产党根本不是传说中的土匪,而是非常有文明、有教养的军队。
当然我们也绝对不是那种玩文明范儿的军队,而是接地气的军队和政党,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展中国气派的文明。
比如延安的扭秧歌,那个曲子、歌词就是从民间来的,但是原本的民间的歌词是开车的,新的经过共产党改造的歌词,就保留了里面人民的积极的因素。

实践中的很多精髓往往是我们书斋里的一些历史学家把握不到的,他们喜欢望文生义、闭门造车、大惊小怪,写了不少挺反动的历史著作,错失了我们先人的那种了不起的故事和精神。
还是老一辈的党史专家,比如金冲及、金一南那才是老司机,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著作去感知那个时代的现实。
好,我们今天不自说自话,我要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讲一个国民党的后代的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这位学者名叫邹谠,名字里就有一个党,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他的父亲叫邹鲁。
可能有人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是西山会议派,所以到后来就边缘化了。但是也可能因为他们边缘化,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客观的看法。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刚开始打仗的时候这个邹谠他就去美国读书了,学政治。
后来他在美国写了一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分析国共战争为什么美国失去了作用,退出了中国。
这本书名噪一时,不过他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写的,为美国人提政策建议。但是写的又非常真实,直言不讳美国人的背信弃义。
那么改革开放之后,邹谠先生被北大聘为荣誉教授,因为那时候需要他来帮助我们重建政治学科。
因为几十年前院系调整,主席干脆把政治学科给它砍了,因为觉得你们不接地气,就喜欢搞西方那一套,没啥用。
因为觉得你们不接地气,就喜欢搞西方那一套,要你们何用?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还是恢复了政治学科,那是不是变得有用了呢?大家自己判断,一定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邹谠的这本书叫做《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就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该如何与西方的政治科学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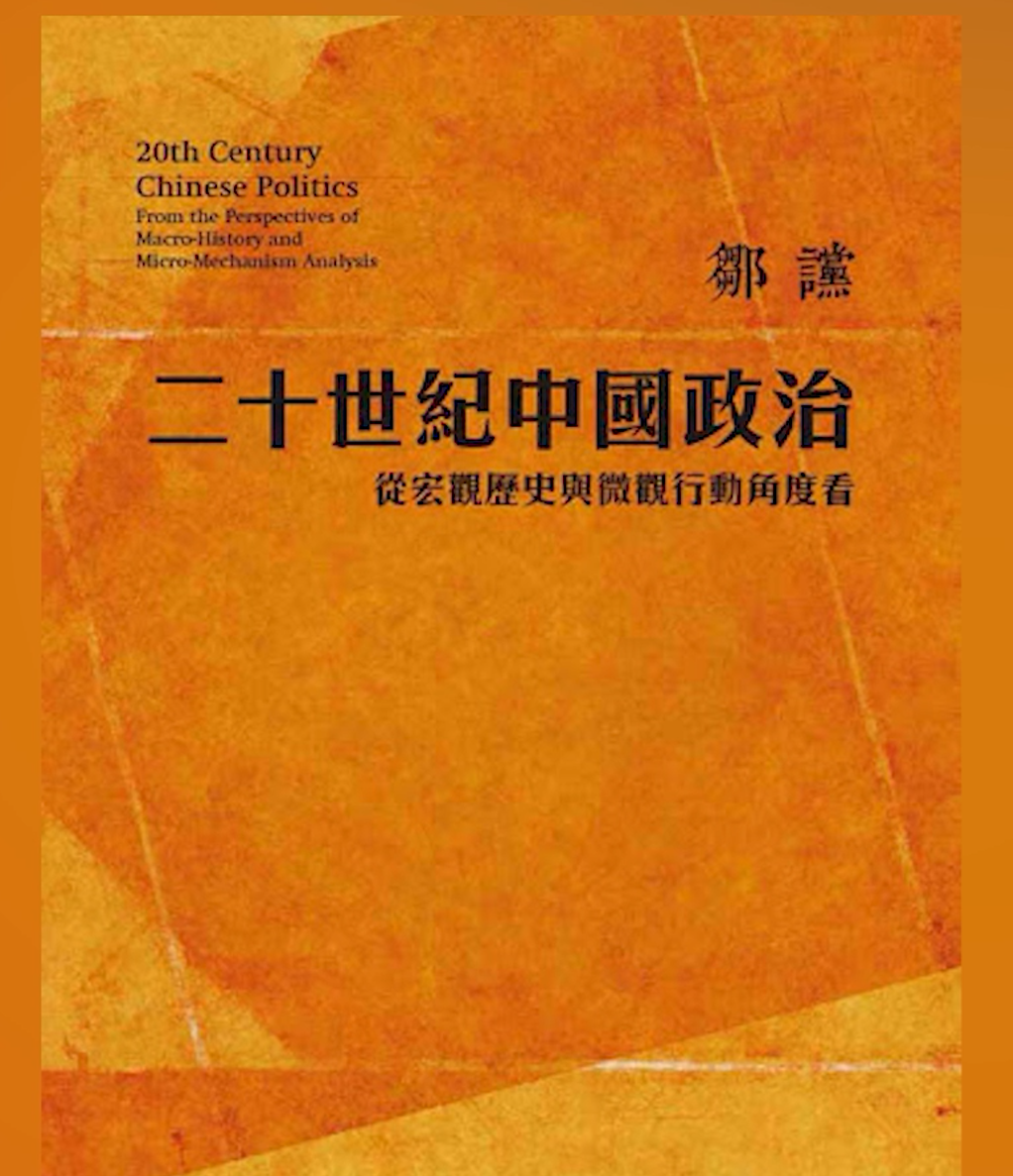
他基本上还是一个调和主义者,不过他的观察视角很有意思,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全能主义,用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特点。
这本书里收录了一篇采访很有意思,记者叫做戴晴,这篇采访发表在《光明日报》1986年8月11日版。
这个戴晴可不是一般的记者,她是红二代,其实她姓叶。
那记者就问邹谠,你是否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极权主义政党?她用的这个词是totalism,邹谠说极权主义其实是另外一个词,叫totalitarianism。
他说那个词是代表极权主义,totalism,我认为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应该翻译成全能主义,全能,十项全能的全能。
他说近代中国遭遇全面的入侵,社会秩序崩塌,经济被破坏,于是礼崩乐坏、社会崩溃、道德沦丧,社会完蛋了。
传统的社会组织,比如乡村社会、道德法律都不管用了,没人管事了,一盘散沙,那怎么办?
有的政党就想我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我把方方面面的责任全部担起来,本来是由社会来管的事情,由我政党来组织。
所以从国民党的孙中山开始,就强调党的组织、党的纪律,他为什么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扶助农工就是要深入社会。
但是国民党没有做成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很快反动后退,只是团结上层阶级,像资本家、地主、大官僚、买办、城市的知识分子。
而共产党深入社会,重新构建各个方面的社会秩序。所以共产党特别强调渗透到基层去,特别强调组织。

邹谠说共产党这样做是带来了彻底的社会革命,也给了底层人机会,让很多普通人有了上升的机会,很多农民做了干部。
我想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我们的祖上都是普通人,我的爷爷辈就是山里的穷人。你想民国的时候有多少有钱人,有多少知识分子,大部分人都是泥腿子。
共产党为了把这个落后的国家组织起来,动员它的一切力量去反帝反封建,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叫做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就好比后来的计划经济的单位,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小孩上学,甚至洗澡,方方面面都管起来,我小时候我们的国企工厂里就有公共浴室,家里是没有浴室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邹谠的这个视角是区别于以往的我们的观察共产党政治的视角。
以往我们可能通过经济制度来观察,你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但是他用了一个政治的视角,你是全能主义,所以你什么都管,而不是说因为你是计划经济,你什么都管。
区别于西方的国家,西方的政府只管某些领域,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你有病你买保险了没有?没有我不管。没有呼吸机怎么办?这就是生活。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西方社会平时的社会组织也比较强,资本也比较强大,有些时候确实可以靠自己。
比如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当中,我们的基层组织仍然能够动员起来,比如居委会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登记发口罩,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居委会的同志也很累。

有些人为了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就会说德国法西斯也号称他们是社会主义,邹谠还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深入社会,但恰恰是为了避免社会革命,就是不想让工人泥腿子翻身,他们用小恩小惠拉拢,用恐怖政治镇压。
而中国发动底层社会革命,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
全能主义也会遇到自己的问题,邹谠说一个是掌握不好,扩大化就会破坏民主。
他举了以前我们的肃反运动和土改扩大化的问题,但他同时又说明全能主义只是表达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它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它也不等于个人崇拜和独裁。
第二个方面邹谠认为全能主义对于建国特别有用,但是一旦建国成功了,全能主义就应该后退,那你就应该像西方一样来搞民主自由。
我觉得邹谠先生还是陷入了西方政治学科的思维,要把全能主义和个人自由对立起来。
我觉得更重要的方面是全能主义也要与时俱进,毕竟我们面对着一个超大规模超多人口的国家,别人的方法不一定好用。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多元,社会越来越复杂,全能主义确实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方面,因为你管得过来吗?
我们说全能主义深入社会生活什么都管,包括婚姻这种事情,党组织也是要管的。
所以那时候想要离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离婚书记就可能来找你做工作,不要随便离婚,现在是不管了,放开了。
80年代有人犯流氓罪就被判死刑了,流氓罪那就是男女关系。确实那一段有些让人遗憾,当时跳舞搞男女关系,有可能被枪毙的。
有一个著名的小白脸演员叫迟志强,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事情被抓起来了,其实他做的事情也就和罗志祥是差不多的,还没有他严重,不就是“多人跳舞”嘛,但是他就被抓了。
但是要注意,那时候可真是一刀切。有一个共和国元老,他在军队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他的一个孙子就被枪毙了,就是因为做“多人运动”。
所以当时是统一执法,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国都是这么干的。为什么会这样严格,搞“多人运动”为什么就被毙了?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全能主义的视角去理解,当时的社会控制很严,因为不敢放松,因为一旦放松了你就不好管了。
以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你现在都要管,一方面你自己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容易管出事来。
改革开放让我们逐步地走出了全能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有权威、有组织保持全能主义的积极的一面;
一方面要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大家自己的活力。
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吃力不讨好,对于政党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尴尬。
因为你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别人什么事情都找你,你干了十件好事,有一件事没干好,别人也会怪你。
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政党他会非常的负责,因为这个国家是我建的,我要负责到底,我要和它共存亡,干不好也是我的。
所以不存在两党制那种,干不好就拉倒,那我就下台呗,让他们继续干,他们干不好了你们再选我。
我们借鉴邹谠的观点,又要超越他,全能主义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既不能放弃也不能固守。
比如今天的互联网管理,因为信息网络太复杂多元,充满活力,也充满危险。不管不行,死管也不行。
然而原来的全能主义的条块化的管理机制,是否能适合今天的这种多元的、分布式的、此起彼伏的、新的社会结构和信息传播结构呢?
我来帮助大家学习一下中央文件,比如习近平在统战工作上的讲话,强调要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什么是新的社会阶层?
新媒体人士、专车司机、留学生这些都是,他们都不再属于原来的那种条块化的结构。
比如说原来的出租车司机是属于出租车公司的,现在专车司机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机构,而自媒体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媒体单位。
不像以前不管你是南方的报业,还是北方的报业,都是党的报业。现在的自媒体人士都好像是被腾讯管起来了,腾讯可以封你的号,但是腾讯也不给你发社保。
习近平说要重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没有一致性不行,那样就会乱,但是也不能强行一致。
你要通过学习、鉴别、把握多样性,尊重创造性,重新生长出新的一致性。比如新闻联播说新媒体时代,我们要推行属地管理,什么意思?
就是为了激发地方科层制的动力,这个媒体在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的宣传部门就要管。
可是问题来了,比如说腾讯它公司在广东,属于广东省地方管,可是我们知道腾讯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的巨无霸企业。
这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是新时代我们要设法调整全能主义和网络化社会关系的方向。
顺带说一下,我有不少宝贵的电子书,比如党史材料,存在百度网盘上。
百度网盘在技术上挺好用,但是显然有些不通事理:我的一些电子书突然就不能下载了,系统提示我说有屏蔽词,你们百度也这样全能吗?这样怎么让人信任呢?
我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就是个人账号上传的自己的文件,个人账号是可以下载的,只要他不去传播分享,我已经通过邮件提了建议,但你们没有反馈。
他清醒地意识到人民和公民的区分,他认为西方的政治社会是建立在公民这个概念上的,而共产党的政治社会是建立在人民这个概念上的。
我们知道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反帝反封建,比如为了中华复兴团结起来,才叫做人民。
西方宣称完美的公民社会一旦面对疫情就阵脚大乱,而我们要探索的是全能主义能够让我们快速动员起来抗击疫情,但是又如何能快速的恢复到日常生活和恢复生产。
所以人民和公民、全能主义和个人权利、斗争和日常生活,它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平衡。
人民和公民、全能主义和个人权利、斗争和日常生活,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也不可能偏废任何一方。
我们还是要强调共产党的那种面对永恒斗争的精神,一味地希望岁月静好是危险的。
如今天下熙熙攘攘,很多地方大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必须还要继续全能呀!
在建党99周年之际,祝愿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能够协力共进、与时俱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