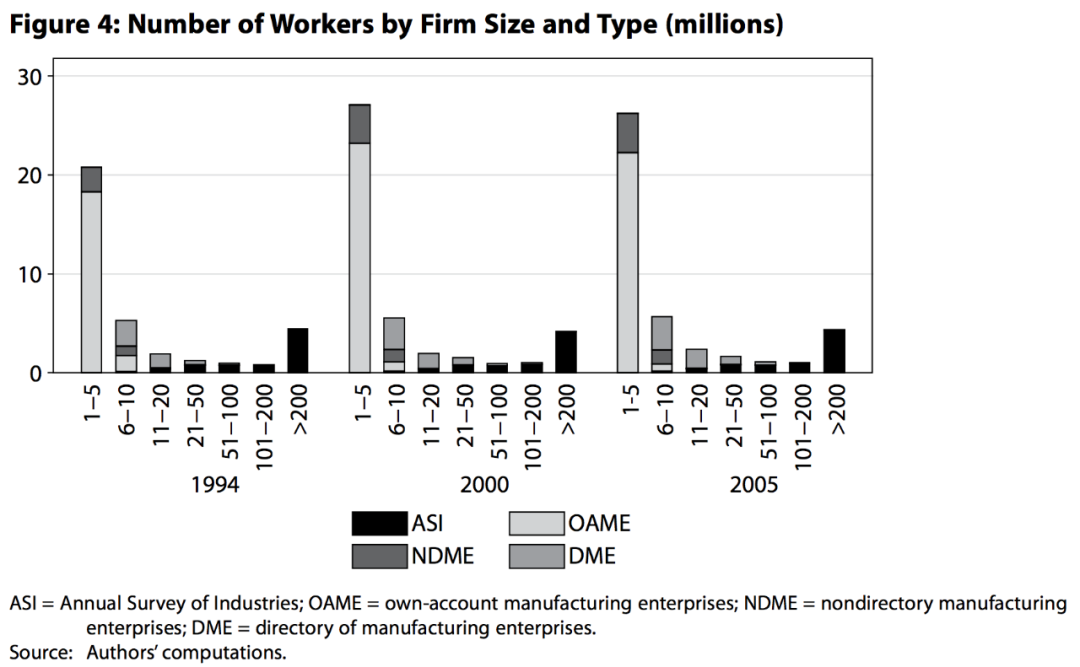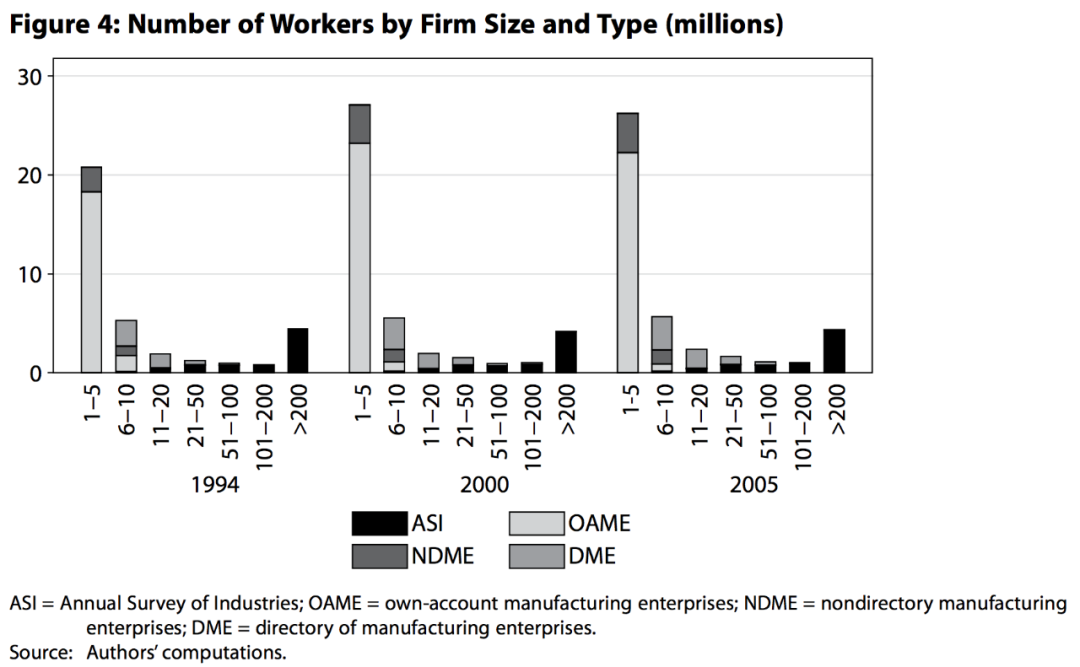在我刚进入投资行业的时候,前辈在第一天就提问了一个问题:投资的本质是什么?我想了几个答案,投资是投企业、看盈利、做复利等等,但都不那么令人满意。而前辈给出的结论是,投资是认知的变现。盈利只是结果,认知才是根本。 这个答案我揣摩体会了好几年,而当我继续成长之后,才更加深刻体会到,何止是投资,工作、生活甚至人生,基本都是认知的“变现”。于是,我便喜欢了研究这项工作,因为这可以提升认知,是有意义的。 而聚焦中国,无论投资、创业、工作、生活,所有认知的基石,便是如何理解中国、理解影响中国经济、产业的因素。在过去一年,有三大因素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中国产业链是否会转移出去?芯片被卡脖子是否有出路?自主创新到底行不行? 而理解这些,便能尽可能贴近科技产业的真实脉搏。 恰好,在年底,我也观看了 罗振宇2021 “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关于上述三个问题都有所涉及。关于产业链罗振宇讲了一个印度小伙的故事;关于芯片和自主化,也带来了产业一线的研发、采购的信息。这些素材就像一块块小拼图,为我们理解三个话题提供了更完整的画面。新年伊始,我们便从这三个角度来进行探讨,寻找认知的基石。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依托人口红利、供应链丰富度、产业深度等等,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在中美摩擦之下,中国产业链转移出去的担忧开始加剧。一般认为有两大腹地可以承接:一个是印度;另一个则是越南。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不太行。 先来看看印度。 “印度超越中国”的声音这么多年来也从未间断,著名美籍经济学家黄亚生就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黄教授从1995年开始就为印度崛起摇旗呐喊,“龙象之争”的说法也算是他提出来的。2015年,黄亚生做客许知远的节目,谈及印度时说:中国哪个方面都比印度优越,除了制度。 国内舆论对印度的看法,一直有种两极分化的特征。一方认为印度有人口红利,也有更加市场化的制度,极具发展潜力。另一方则认为满分100考40,当然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但这么多年下来,似乎也没上及格线。事实上,从各项经济数据上看,印度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国。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世界人口综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测算,印度去年的GDP将达到2.94万亿美元,超越英法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差不多是中国2004年的水平。而在衡量工业水平的三大硬指标:发电量、钢铁产量和煤炭生产上,印度的煤炭钢铁产量仅次于中国,发电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而制药、IT和电影工业是印度的三大王牌产业,贡献了超过10%的GDP,却也有着两个关键的缺陷。 首先,这三大产业始终是国内精英的独自狂欢,其价值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底层人民。其次,由于产业链长度和专业性的限制,注定了这三大王牌产业只能吸纳一小撮就业,三者合计不过千万人。较之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实在是杯水车薪。 同时,如果看印度的制造业统计图,会发现有90%的“公司”其实都是一家几口齐上阵的小作坊。而且,印度发展制造业,在法律上有枷锁:比如著名的MGNREGA,即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障法,就承诺为每个申请人在当地提供100 天的非熟练就业机会,如果15 天内不解决就业,政府还必须提供一定的失业津贴。 资源禀赋上有先天缺陷:虽然矿产种类丰富,却缺乏制造业的关键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储量46 亿桶,差不多是中国的1/6;印度冶金煤储量337亿吨,仅为中国的3%。 罗振宇在演讲中,也讲了一个故事,中国老板在印度有个工厂,提拔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印度小伙,但没想到被提拔后小伙却遭到打骂,因为这小伙子是个低种姓,“上不得台面”。这也指向了在经济、技术之外,持续压制印度人口红利爆发的重要枷锁:印度“种姓”制度。这是非常关键、却又难以变更的社会因素。 2004年,韩国制造业巨头浦项制铁打算在印度兴建工厂,媒体惊呼“印度势头直逼中国”。然而之后的12年,浦项制铁相继经历了合作伙伴退出、农民抗议征地、许可证审批受阻、当地政府干预投资等等一条龙服务,最终在2016年宣布放弃建厂计划。 这12年的时间, 见证了一家雄心勃勃的制造业巨头,在印度逐渐耗尽耐心,最终败走的全过程,也恰似印度制造业屡战屡败的缩影。印度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本质,在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创造适应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其难点不在“创造”,而在“打破”。对于当前的印度而言,并非易事。 而越南同样无法对中国构成威胁。 越南发展基本都是靠外资,先是日本、韩国(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最近几年也多了中国企业。而越南的优势归结起来主要是:零关税政策多、地理位置优势、以及目前仅为中国三分之一薪酬的人口红利。但,这些优势也并不稳定。 劳动力方面,越南毕竟“只”拥有1亿人口,相比中国和印度的14亿要逊色不少,这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虽然存在,但总量不大。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水涨船高,前几年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近两年增速也有5%-7%,赶上中国可能也就是三五年时间。同时,适龄劳动人口的数量也已出现拐点。 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税收优惠力度仍然诱人,但蜂拥而至的厂商推高了土地价格。2019年,南部胡志明市的工厂租金平均达到4.1美元/平米,北越经济圈也有3.5-4美元,与之相比,苏州是4.2美元,东莞只有3.6美元,而越南的水电价格也要高于中国。 因此,施展教授便认为,越南电子产业是“两头在外”的“半体外循环”状态,是中国产能的“溢出”而非“转移”。看来,印度、越南,做东莞可能可以,但做深圳还不行。 2020年8月,华为公开表示海思麒麟高端芯片已经“绝版”,中国最强的芯片设计公司,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锁死了未来,也令“卡脖子”问题更加突出。 虽然美国半导体行业产值大约占全世界的47%,体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但韩国、欧洲、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其他“豪强”也各有擅长,与美国的差距并不是无法越过的鸿沟。 比如,韩国 在产值1500亿美金的存储芯片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双强(三星、海力士)占据65%市场;欧洲 在模拟芯片领域有三驾马车(英飞凌、意法半导体、恩智浦),从80年代起就从未跌出全球二十强。 日本 不但有独步天下的图像识别芯片,以信越日立为首的几家公司,更是牢牢扼住了全世界半导体的上游材料。中国台湾在千亿美元级别的芯片代工领域,更胜美国一筹,台积电和联电占据60%的规模,以日月光为首的封测代工也能抢下50%的市场; 中国大陆依托庞大的下游市场,近年芯片设计领域发展迅速,不但诞生了世界前十的芯片设计巨头华为海思,整体芯片设计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二;芯片封测更是有了长电等国际前列。 看似一超多强,但美国禁令一出,其他国家纷纷遵守,中国大陆面临巨大压力。而大家忌惮的,其实是美国手里的两张半王牌:芯片设备、设计工具、以及材料。 半导体设备商,不仅提供设备卖铲子,还要全程服务卖脑子,可谓是芯片制造商的外置大脑。 根据2019年资料,全球前五大半导体设备商占据了全球58%行业营收。其中,美国独占三席;其余两席,一席是日本的东京电子,另一席荷兰的阿斯麦,恰巧,这两家又都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 美国靠着多年的“时间积累”和超高精密度“工艺技术”,在设备领域形成了牢牢的主动权。而时间和技术,都不是后进者可以一蹴而就的。 设计方面,素材库、IP库、以及仿真验证,对芯片制造至关重要。加州大学教授有一个统计测算,2011年一片SoC的设计费用大概为4000万美元,而如果没有EDA,设计费用则会飙升至77亿美元,增加了近200倍。 设计是芯片产业的高杠杆。 我国最大的EDA厂商华大九天在全球的份额差不多是1%,而美国三大厂商Synopsys(新思科技)、Cadence(楷登电子)以及Mentor Graphics(明导科技,2016年被西门子收购)则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 其实单纯写出一套软件,难度并不大。关键还是要有海量丰富的IP、PDK,以及产业上下游的支持配合。单点突破未必有效,需要军团全面突围。 而材料领域,无论提纯、还是配方,基本的理论原理、工艺技术都不是难事儿。但如何选材、配比,从而实现极致的效果,却需要高度依赖经验法则,即业内常说的 “know-how” 。 梳理了芯片被卡脖子的领域之后,可以发现,与其说芯片是个科学问题,倒不如更是个工程学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途径:一个是采用正确的心态,保持自主攻关的同时,也要继续保持对外开放;另一个是正确的方式,把一个个具体的挑战,拆解成庞大的工作量,然后靠资金、资源、人才、时间、耐心、决心,一口一口地吃下来。而更为重要的,就是加大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投资和精力。 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费用,在全年总研发支出中仅占5%,而这还是10年来占比最高的一年。而同期美国基础研究占比则是17%,日本是12%。正如任正非所言,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只有实现基础技术能力的创新突破,以及与工程能力的大会师,才能赢取下一个时代。 2018年,被誉为“中关村才女”的梁宁,写了一篇关于操作系统和芯片往事的文章,被产业界一致认可。这其中便提到了我国关于自主创新态度的摇摆不定。有人觉得我们不行,做不出来;有人说造不如买、反正都能买到。这种争议纠结,在操作系统领域非常突显、令人扼腕。 倪光南从上世纪90年代、PC时代就奔走呼吁自主系统;而王坚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虽然时代变了、行业的海外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还是没有一款能打的产品出来。而回顾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五大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 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PC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5个自主芯片,3个自主系统,那就是15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 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IBM的联想、最大的PC市场;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201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 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 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 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可能还是我们自己的态度。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但幸运的是,梁宁从一线而来的感受便是,自主创新的战略决心是铁板钉钉的。 共识的背后,意味着一张张的订单,一笔笔的投资,一个个的政策,放在做好准备的人的面前。比如国产的统信OS,已完成全部适配的应用包括不少日常高频使用的桌面软件,如:搜狗输入法、金山WPS、QQ、微信、钉钉等等。而海外软件,几乎都找到了一一对应的替代品。华为、龙芯也都是合作伙伴。 中国科技虽然有短板,但是并没有缺环。几乎所有的被卡脖子的领域,都有国产替代企业。未来,这些卡脖子清单,都会转化为机会清单。这是一个充满期待、也值得期待的未来。 在这场跨年演讲中,罗振宇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也很有趣,同事在机场对罗振宇说,“这块牌子(党员先锋岗),老外要是能理解得了,才算真的理解了中国。” 这个小故事,指向的正是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内生组织力。 这是一张被组织起来的网络,既对内又对外。这张网络规模庞大、层次丰富、密密匝匝,既有强度,又有弹性。这是我们面对疫情、走出疫情的勇气和实力,也是面对卡脖子、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 而理解组织力、凝聚力下的中国,是我们所有认知的基石。这也许就是高瓴、景林、红杉等众多投资公司押注中国的原因,也是无数海外企业想尽方法在中国开店办厂找伙伴的诱惑,更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拼搏奋斗的憧憬和动力。
上一篇谷火平:运-20现身永暑礁!— 1200公里外,山东舰和075投入演习 |2021-01-06
下一篇军榜:中国唯一的海洋霸权是怎么建立的 |2021-01-06